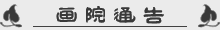 |
 画院资讯 画院资讯 |
| 天津南开画院 - 画院资讯 - 端坐我不端坐心 |
端坐我不端坐心 端坐我不端坐心
——记画家孟宪锋的禅意世界
美术批评的正常流程,应该是实现评论者自发、自觉地对所见作品做出赏析、阐发和推介。与名声无关,与润资无关,与稿酬无关,与市场无关,与利害无关,与人情关系无关。不能是应景的,不能是违心的。也不应该是言过其实、讨好献媚的,或者“扯虎皮,拉大旗”,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职位名头来作势。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写作者、画家、媒体人自作聪明地搞一点手腕和“运作”,终究是缺乏自尊和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美术批评是画家作品和大众鉴赏之间的桥梁,它本身的氛围健康与否,既与公共文化环境有关,也与评论家、画家本身的正当利益有关。正心,正艺,正文,是需要诸方面来谨记的。
在以上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我乐于为宪峰老师写一些评论其绘画艺术的文字,并为此深感荣幸。
初识宪锋,就觉得他有禅师的特质。
但他也是个很矛盾的个体。我能感觉到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多侧面并存,所带给他的消耗。可是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总能从各种当下境况中超脱出来并重新站立于他业已形成的精神原点;或者务宁说他原本就不用挣脱而径直就处在那个“原点”之上。那是个惬意而自如的孟宪锋,一个不为他的大多数朋友和身边人所了解的孟宪锋。
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关注,使他简捷的话语很少有知味者。他偶尔面对着文化落差很大的人来闲聊时,或者反倒他是显得力不从心的;或者又是鱼游于水的那种从容和容余。
对于禅意的现代解释,必定应该是开放性的。即可能性很多,不必做硬性统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可各自领会,各取所需。不过,但凡上了点年纪的人,可能大都容易接受这样的“参禅”心境:宁定,安适,不为外物所扰。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禅意应该是与一些很具体的人生经历——或者叫做“岁月”吧——有关的。不然你去“参”什么呢?
内心入“静”才能涵养真如心。真如心之动转并落实在行动上,才是所谓的“动”。这是一个静、动一体的哲理。这可能也是禅宗思想的精髓。《坛经》讲到过定与慧的一体性的关系:入定、入静,才能得见自性和良知,进而才能生慧、生动。良知在定与慧之间的这个纽带作用,是我向宪峰老师谈及过的。
毫无疑问,良知是行动的原动力。由此,不妨再说一遍:正心,正艺,正文,是需要大家谨记的。
中国画大约经历了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时期和文人画时期。中国的佛道人物画,第一个大家是南北朝的张僧繇。那个时候绘画的宗教功能已经是主流。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是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佛教对中国画的发展,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与张僧繇有关的一个成语“画龙点睛”,似乎在暗示这样一个事实:佛教的熏染,并不抵消或取代中国画家的中华文化的属性。这种属性意味着中国画一定是有关于“情理交融”的、意向性的、开放性的民族情感样式的,而这种样式的最高体现一定在士人阶层即文士那里。所以中国第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顾恺之为什么是紧跟着张僧繇后踵而出现的,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张僧繇的绘画创作题材并不仅仅限于佛道人物。单就人物画来讲,从他下来,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直到现代的刘继卣,范曾,是一个路子,以描为主,很端庄,是“古典”的;任伯年,刘国辉,方增先是一个路子,重“笔”;梁楷,黄慎,李世南,吴山明是重“墨”的一路;贯休,陈洪绶是一个路子,特点是求怪。施大畏如中国画的“巴洛克”,动感十足。梁岩是对一个形象有所触动了才会动笔,算是唯美主义写生派里的佼佼者。宪锋老师则不受任何限制,心有妙悟,全出己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和风格。他画的禅宗和尚,脸有笑容而不自知,这是发自内心的笑。姿态上绝不是正襟端坐的传统大乘教派的佛像,而是或行或卧或伸懒腰或拍肚腹的,姿态各异面貌活脱有趣的世间佛,完全符合禅宗的对世俗价值的归属感。这可能算是一种外松内紧吧,所谓嬉笑横斜之间,佛自在心中,心本来端庄。面貌的描画非常工整,继承了津门人物画的大传统;衣服的表现则笔墨味道十足,炉火纯青的速写功底得以笔墨形式的展现。恐怕在当今从事中国画的人当中,西画修养无有出其右者,但他非常知道约束自己,只在人物面部、手臂的设色上表现出一点光影、体面的效果。其实他也是有意为此,来求一份新意。在画大创作时,他则不再使用生宣了,为了实现自己别出心裁的效果,他选用熟宣;设色上不回避西画式造型的手法,也会用在皮肤色之外的区域。宪锋老师诸如此类的探索,是不是令他本人满意了,我想答案极有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一个创作者永远是一个“在路上”的状态;他的探索是不是最终会获得里程碑意义的成功,恐怕只有让时间来交出答案了。
作者;范迪安、柳长松
|